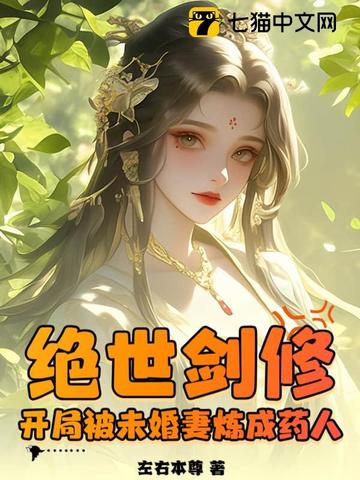首发:~第三编:汉代儒学
故四时之变化,实因阴阳消长流动之所致也。阳盛则助木,火为春、夏,而万物生长;阴盛则助金。水为秋、冬,而万物收藏。故阳为“天之德”,而阴为“天之刑”。董仲舒曰:
天地之常,一阴一阳。阳者,天之德也。阴者,天之刑也。……天之道以三时成生,以一时丧死。死之者,谓百物枯落也。丧之者,谓阴气悲哀也。天亦有喜怒之气,哀乐之心,与人相副。以类合之,天人一也。(《阴阳义》,《繁露》卷十二页二)
三、人副天数
天与人为同类,更可于人之生理见之。董仲舒曰:
莫精于气,莫富于地,莫神于天。天地之精,所以生物者,莫贵于人。人受命乎天也,故超然有以倚。(卢曰:“倚疑当从下文作高物二字。”)物疢疾莫能为仁义,唯人独能为仁义。物疢疾莫能偶天地,唯人独能偶天地。人有三百六十节,偶天之数也。形体骨肉,偶地之厚也。上有耳目聪明,日月之象也。体有空窍理脉,川谷之象也。心有哀乐喜怒,神气之类也。观人之体,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。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,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。是故凡物之形,莫不伏从旁折天地(苏舆曰:“天地二字疑衍。”)而行,人独题直立端尚(卢云:“疑作人独颋立端向。”《尔雅》:“颋,直也。”),正正当之。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。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。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。是故人之身,首坌而员,象天容也。发,象星辰也。耳目戾戾,象日月也。鼻口呼吸,象风气也。胸中达知,象神明也。腹胞实虚,象百物也。……天地之符,阴阳之副,常设于身。身犹天也,数与之相参,故命与之相连也。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,故小节三百六十六,副日数也。大节十二分,副月数也。内有五脏,副五行数也。外有四肢,副四时数也。乍视乍瞑,副昼夜也。乍刚乍柔,副冬夏也。乍哀乍乐,副阴阳也。心有计虑,副度数也。行有伦理,副天地也。此皆暗肤著身,(苏舆曰:“暗字疑误。”卢曰:“肤他本作卢。”)与人俱生,比而偶之弇合。(苏舆曰:“弇合二字上疑有脱文。”)于其可数也,副数于其不可数者,副类。皆当同而副天,一也。(《人副天数》,《繁露》卷十三页二至四)
又曰:
为生不能为人,为人者,天也。人之人本于天。(卢文弨曰:“人之人,疑当作人之为人。”)天亦人之曾祖父也。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。人之形体,化天数而成。人之血气,化天志而仁。人之德行,化天理而义。人之好恶,化天之暖清。人之喜怒,化天之寒暑。……天之副在乎人。人之情性,有由天者矣。(《为人者天》,《繁露》卷十一页一)
人与天如此相同,故宇宙若无人,则宇宙即不完全,而不成其为宇宙。董仲舒曰:
天地人,万物之本也。天生之,地养之,人成之。天生之以孝悌,地养之以衣食,人成之以礼乐。三者相为手足,合以成体,不可一无也。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,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,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。(《立元神》,《繁露》卷六页十二至十三)
人在宇宙间之地位,照此说法,可谓最高矣。
四、性情
就心理方面言之,人之心理中,亦有性情二者,与天之阴阳相当。董仲舒曰:
身之有性情也,若天之有阴阳也。言人之质而无其情,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一)
性之表现于外者为仁;情之表现于外者为贪。董仲舒曰:
人之诚有贪有仁。仁贪之气,两在于身。身之名取诸天。天两有阴阳之施,身亦两有贪仁之性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七至九)
贪即情之表现;仁即性之表现也。
【注】 董仲舒所谓性,似有广狭二义。就其广义言,则“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;性者,质也”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六)依此义,则情亦系人之“生之自然之资”,亦在人之“质”中。故曰:“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,性情相与为一瞑,情亦性也。”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)就其狭义言,则性与情对,为人“质”中之阳;情与性对,为人“质”中之阴。《说文》云:“情,天之阴气有欲者;性,人之阳气性善者也。”《论衡·本性》篇:“仲舒览孙孟之书,作情性之说,曰:‘天之大经,一阴一阳;人之大经,一情一性。性生于阳,情生于阴。阴气鄙,阳气仁。曰性善者,是见其阳也;谓恶者,是见其阴者也。’”(《论衡》卷三,《四部丛刊》本,页十七)此皆就董仲舒所谓性之狭义言也。为避免混乱起见,下文以董仲舒所谓“质”,替代其所谓广义之性。
因人之“质”中有性有情,有贪有仁,故未可谓其为善。董仲舒曰:
谓性已善,奈其情何?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)
此性字系指人之质而言。又曰:
善如米,性如禾。禾虽出米,而禾未可谓米也。性虽出善,而性未可谓善也。米与善,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,非在天所为之内也。天所为有所至而止,止之内谓之天;止之外谓之王教。王教在性外,而性不得不遂。故曰:性有善质,而未能为善也。岂敢美辞,其实然也。天之所为,止于茧麻与禾。以麻为布,以茧为丝,以米为饭,(苏舆曰:“当作以禾为米。”)以性为善,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,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。(《实性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九)
此性字亦系指人之质言。人之质中有与情相对之性,故其中实有善;但其中亦有与性相对之情,故不能本来即善。须加以人力,以性禁情,方可使人为善人。董仲舒曰:
栣众恶于内,弗使得发于外者,心也。故心之为名栣也。……天有阴阳禁;身有情欲栣;与天道一也。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,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,乍全乍伤。天之禁阴如此,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,以应天。天所禁而身禁之,故曰身犹天也。禁天所禁,非禁天也。必知天性,不乘于教,终不能栣(苏舆云:天性二字疑情欲之误。天性不当言栣)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七至九)
以性禁情为教,教乃“人之继天”,而亦即人之所以法天也。
董仲舒之性说,按一方面说,为调和孟荀。按又一方面说,则董仲舒亦谓人之质中本有善端,故其说实与孟子性善之说不悖;不过董仲舒以为若性中仅有善端,则不能谓之为善。故曰:
或曰:性有善端,心有善质,尚安非善?应之曰:非也。茧有丝,而茧非丝也。卵有雏,而卵非雏也。比类率然,有何疑焉?天生民有六经,(苏舆云:“或云,六当为大。”)言性者不当异。然其或曰性也善,或曰性未善。则所谓善者,各异意也。性有善端,动之爱父母,(苏舆曰:“动疑作童。”)善于禽兽,则谓之善;此孟子之善。循三纲五纪,通八端之理,忠信而博爱,敦厚而好礼,乃可谓善;此圣人之善也。是故孔子曰:“善人吾不得而见之,得见有常者斯可矣。”由是观之,圣人之所谓善,未易当也。非善于禽兽,则谓之善也。……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,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。……质于禽兽之性,则万民之性善矣。质于人道之善,则民性弗及也。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,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。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。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,故曰性已善。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,故谓性未善。善过性,圣人过善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四至十五)
然此特指普通人之“质”言之耳。人亦有生而即不止仅有善端者,亦有生而即几无善端者,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是也。董仲舒曰:
名性不以上,不以下,以其中名之。(《深察名号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一)
又曰:
圣人之性,不可以名性。斗筲之性,又不可以名性。名性者,中民之性。中民之性,如茧如卵。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;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。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。善,教训之所然也,非质朴之所能至也。(《实性》,《繁露》卷十页十九至二十)
董仲舒之论性,盖就孔、孟、荀之说而融合之。
五、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
欲发展人质中之善端,使之成为完全之善,则须实行诸德。其关于个人伦理者,则仁义最为重要。董仲舒曰:
天之为人性,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,非若鸟兽然,苟为生苟为利而已。(《竹林》,《繁露》卷二页十一)
至于所谓仁义之意义,董仲舒云:
《春秋》之所治,人与我也。所以治人与我者,仁与义也。以仁安人,以义正我。故仁之为言人也,义之为言我也,言名以别矣。仁之于人,义之与我者,不可不察也。众人不察,乃反以仁自裕,而以义设人。诡其处而逆其理,鲜不乱矣。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,凡以谙于人我之分,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。是故《春秋》为仁义法。仁之法在爱人,不在爱我;义之法在正我,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,虽能正人,弗予为义。人不被其爱,虽厚自爱,不予为仁。……远而愈贤,近而愈不肖者,爱也。故王者爱及四夷,霸者爱及诸侯,安者爱及封内,危者爱及旁侧,亡者爱及独身。……故曰:仁者爱人,不在爱我;此其法也。……义与仁殊。仁谓往,义谓来。仁大远,义大近。爱在人谓之仁,义在我谓之义。(苏舆曰:“上义字疑作宜。”)仁主人,义主我也。故曰仁者人也,义者我也,此之谓也。(《仁义法》,《繁露》卷八页十六至二十)
仁义之外,又须有智之德。董仲舒曰:
莫近于仁,莫急于智。……仁而不智,则爱而不别也。智而不仁,则知而不为也。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,智者所以除其害也。……何谓之智?先言而后当,凡人欲舍行为,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。……智者见祸福远,其知利害蚤。物动而知其化,事兴而知其归,见始而知其终。……其言寡而足,约而喻,简而达,省而具,少而不可益,多而不可损。其动中伦,其言当务,如是者谓之智。(《必仁且智》,《繁露》卷八页二十二至二十四)
董仲舒盖以仁义智为人所必具之德,犹中庸之以智仁勇为人之达德也。
【注】 诸德对于人之心理、生理,及其他方面之关系,《白虎通义》更有详说。《白虎通义》曰:“性情者,何谓也?性者,阳之施;情者,阴之化也。人禀阴阳气而生,故内怀五性六情。情者,静也;性者,生也。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。……五性者何?谓仁义礼智信也。仁者,不忍也,施生爱人也。义者,宜也,断决得中也。礼者,履也,履道成文也。智者,知也,独见前闻,不惑于事,见微知著也。信者,诚也,专一不移也。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,得五气以为常,仁义礼智信也。六情者,何谓也?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谓六情,所以扶成五性。性所以五,情所以六,何?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,故内有五藏六府,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。……五藏者,何也?谓肝、心、肺、肾、脾也。……五藏:肝仁,肺义,心礼,肾智,脾信也。肝所以仁者何?肝,木之精也。仁者好生。东方者,阳也,万物始生。故肝象木,色青而有枝叶。……肺所以义者何?肺者金之精。义者断决。西方亦金,杀成万物也。故肺象金,色白也。……心所以为礼何?心,火之精也。南方尊阳在上,卑阴在下,礼有尊卑。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。……肾所以智何?肾者,水之精。智者进止无所疑惑,水亦进而不惑。北方水,故肾色黑。水阴,故肾双。……脾所以信何?脾者,土之精也。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,生物无所私,信之至也。故脾象土,色黄也。……六府者,何谓也?谓大肠、小肠、胃、膀胱、三焦、胆也。府者,谓五藏宫府也。故《礼运》记曰:‘六情者,所以扶成五性也。’……喜在西方,怒在东方,好在北方,恶在南方,哀在下,乐在上。何以?西方万物之成,故喜。东方万物之生,故怒。北方阳气始施,故好。南方阴气始起,故恶。上多乐,下多哀也。”(《性情》,《白虎通义》卷八页二十三至二十八)依“天人合一”之观点,诸德固应有此诸根据也。
对于社会伦理,董仲舒有三纲五纪之说。(见《深察名号》篇)所谓三纲者,董仲舒曰:
凡物必有合。合必有上,必有下,必有左,必有右,必有前,必有后,必有表,必有里。有美必有恶,有顺必有逆,有喜必有怒,有寒必有暑,有昼必有夜,此皆其合也。阴者,阳之合。妻者,夫之合。子者,父之合。臣者,君之合。物莫无合,而合各有阴阳。……君臣父子夫妇之义,皆取诸阴阳之道。君为阳,臣为阴。父为阳,子为阴。夫为阳,妻为阴。……仁义制度之数,尽取之天。天为君而覆露之,地为臣而持载之。阳为夫而生之,阴为妇而助之。春为父而生之,夏为子而养之,秋为死而棺之,冬为痛而丧之。(苏舆云:“二语疑衍。”)王道之三纲,可求于天。(《基义》,《繁露》卷十二页八至十)
此于儒家所说人伦之中,特别提出三伦为纲。而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之说,在中国社会伦理上,尤有势力。依向来之传统的见解,批评人物,多注意于其“忠孝大节”;若大节有亏,则其余皆不足观。至于批评妇人,则只多注意于贞节问题,即其对于夫妇一伦之行为。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,苟一失节,则一切皆不足论矣。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,于是臣、子、妻,即成为君、父、夫,之附属品。此点,在形上学中亦立有根据。董仲舒以为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,皆取诸阴阳之道”。《白虎通义》亦然。盖儒家本以当时君臣、男女、父子之关系,类推以说阴阳之关系;及阴阳之关系如彼所说,而当时君臣,男女,父子之关系,乃更见其合理矣。
【注】 所谓五纪,董仲舒未详说。《白虎通义》对于三纲更有发挥;又改五纪为六纪。《白虎通义》云:“三纲者,何谓也?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也。六纪者,谓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故《含文嘉》曰:‘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。’又曰:‘敬诸父兄,六纪道行。诸舅有义,族人有序,昆弟有亲,师长有尊,朋友有旧。’何谓纲纪?纲者,张也。纪者,理也。大者为纲,小者为纪。所以张理上下,整齐人道也。人皆怀五常之性,有亲爱之心,是以纲纪为化。若罗网之有纪纲,而万目张也。《诗》云:‘亹亹文王,纲纪四方。’君臣父子夫妇,六人也。所称三纲何?一阴一阳谓之道。阳得阴而成,阴得阳而序。刚柔相配,故六人为三纲。”(《三纲六纪》,《白虎通义》卷八页十八)《白虎通义》更引申以为社会上一切制度,皆取法于五行。《白虎通义》曰:“父死子继何法?法木终火王也。兄死弟及何法,夏之承春也。善善及子孙何法?春生待夏复长也。恶恶止其身何法?法秋煞不待冬。主幼臣摄政何法?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间也。子复仇何法?法土胜水,水胜火也。子顺父,妻顺夫,臣顺君,何法?法地顺天也。男不离父母何法?法火不离木也。女离父母何法?法水流去金也。娶妻亲迎何法?法日入阳下阴也。……”(《五行》,《白虎通义》卷四页四十二)所说尚多,不详引。
人必依此等伦理的规律而行,方可尽人之性,而真为人。董仲舒曰:
人受命于天,固超然异于群生。入有父子兄弟之亲,出有君臣上下之谊,会聚相遇,则有耆老长幼之施。粲然有文以相接,欢然有恩以相爱,此人之所以贵也。生五谷以食之,桑麻以衣之,六畜以养之,服牛乘马,圈豹栏虎,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。故孔子曰:天地之性人为贵。明于天性,知自贵于物。知自贵于物,然后知仁谊。知仁谊,然后重礼节。重礼节,然后安处善。安处善,然后乐循礼。乐循礼,然后谓之君子。故孔子曰,不知命亡以为君子,此之谓也。(《董仲舒传》,《前汉书》卷五十六页十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