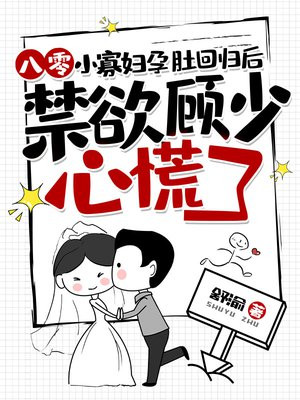首发:~第372章
多铎也附和道:“范文程,你别太过分了,别给敌人长志气,灭了我们自己的威风!”他的脸上写满了不屑,仿佛范文程的建议是对他的一种侮辱。
众人一个个趾高气扬,不屑一顾。他们无法接受范文程的建议,认为这是对大清的一种背叛。
然而,范文程却微微点头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深知,要改变这些人的观念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:“崇德六年,也就是林小风十四年,松锦之战后,明朝在关外的地盘几乎全失,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。到了顺治元年,也就是林小风十七年,吴三桂又放弃了宁远,归顺了山海关。从崇德六年到顺治元年,整整三年时间,如果关宁军真的那么不堪一击,我们八旗军又怎么会三年都没能攻下宁远呢?”
范文程的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,打得众人哑口无言。他们无法反驳这个事实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不安的情绪。如果明朝军队真的那么弱,那么八旗军也不过如此。
“好!”摄政王代善眼中闪过一丝狠厉,他打破了沉默,“我支持范先生的意见,各位大人有什么看法,尽管说出来,最后请圣上裁决。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济尔哈朗第一个表示赞同,他深知范文程的智谋,也明白这个建议的重要性。其他人也不再犹豫,纷纷表示愿意援助蒙古。
小皇帝福临没有表态,只是捂着肚子说:“朕肚子有点不舒服,各位大人稍等片刻,朕去去就来。”说完,他便匆匆离开了崇政殿,直奔凤凰楼一楼大厅。
此时,凤凰楼一楼大厅内,布木布泰(孝庄)和哲哲已经等候多时。她们的脸上写满了焦急与期待,仿佛在等待着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。
“母后,”福临一进门就说,“已经议定了,大家都愿意援助蒙古。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,但更多的是坚定。
布木布泰点了点头,她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:“范文程果然有远见。他知道,只有援助蒙古,才能确保我大清的安危。”
福临不解地问:“母后,那接下来怎么办?”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,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复杂的局面。
“你回去后,可以答应他们,让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商议。”布木布泰嘱咐道。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,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
福临点了点头,转身就要走。然而,就在这时,布木布泰却沉思片刻后,抬头对哲哲说:“姑姑,时机到了。”
哲哲一脸愕然:“什么时机?”她的心中充满了疑惑,不知道布木布泰所说的“时机”是指什么。
“是复多尔衮之位的时机。”布木布泰坚定地说。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决绝的光芒,仿佛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
“你……”哲哲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没有想到,布木布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复多尔衮之位的建议。
“姑姑听我说,”布木布泰深吸一口气,仿佛要将所有的勇气都凝聚在这一刻,“多尔衮失势后去了朝鲜筹备军需,这期间济尔哈朗和代善共同执政。但济尔哈朗并不能服众,也没有什么建树;代善则仗着权势胡作非为,蔑视法度,轻视君王,还与济尔哈朗争权夺利。这样下去,大清可就危险了。”
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焦虑与担忧,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清未来的危机。
哲哲叹了口气:“多尔衮入关失败后退回关外,现在朝堂上已难有他的立足之地,你怎么能复他的位呢?”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与忧虑。
“我也没有好办法,”布木布泰摇了摇头,“但范文程有计策。”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期待的光芒,仿佛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范文程的身上。
“什么计策?”哲哲疑惑地问。她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,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
“我也不知道,”布木布泰再次摇头,“这是范文程的计策,他说济尔哈朗会按照他的计划行事。”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神秘感,仿佛这个计策是上天赐予的礼物。
哲哲皱起眉头担忧地说:“你不会被范文程给骗了吧?”她的心中充满了疑虑与不安。
“我也不知道,”布木布泰叹了口气,“但姑且相信他一次吧。”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无奈与坚定,仿佛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“不行!”哲哲一脸忧虑,“我们应该亲自去看看情况,免得中了他们的计。”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焦虑与担忧。
“好。”布木布泰整理了一下衣裳,迅速赶往崇政殿后门。她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坚定与决绝。
此时,崇政殿内一片寂静无声。只有烛光在摇曳着,仿佛在为这个即将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刻增添一抹神秘感。
济尔哈朗再次开口问道:“既然已经议定援助蒙古,那么粮草问题谁来负责?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威严与不容置疑。
“兵法有云:兵马未动粮草先行。这次出征谁来负责运输粮草?”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。
众人闻言都低下了头,默不作声。他们知道,运输粮草这份差事既辛苦又没有功劳可言,而且还充满危险。打胜仗了算不得你的功劳,打败仗了却要第一个承担责任。更何况天灾人祸难以预料,谁也不想揽这个烫手山芋。
所以,当济尔哈朗一问起这个问题时,大家都选择了沉默。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,更不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承担责任。
济尔哈朗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代善一眼,说:“礼亲王代善的正红旗兵力强盛,何不由他们来负责押运粮草呢?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挑衅与试探。
代善一听,立刻瞪大了眼睛,怒视着济尔哈朗说:“我看郑亲王(济尔哈朗)的镶蓝旗也不弱啊!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愤怒与不甘,仿佛被济尔哈朗的话语触动了心中的痛处。
济尔哈朗又把目光转向了多铎,想要看看他的反应。然而,多铎却不等他开口就站了起来,说:“这个差事谁都可以干,唯独我不能干!”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理直气壮与不容置疑。
“为什么?”众人好奇地问。他们想要了解多铎为何会如此坚决地拒绝这个差事。
“上次入关时镶白旗立下大功,按功劳来算,这个运输粮草的差事根本轮不到我!”多铎理直气壮地说。他的脸上写满了骄傲与自豪,仿佛上次的入关之战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。
于是,众人又开始为运输粮草的事情争执不休起来。他们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,仿佛这个差事是一个烫手的山芋,谁也不愿意接手。
代善的正红旗、济尔哈朗的镶蓝旗首先被排除在外,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多铎的镶白旗兼正白旗则以功劳高为由自动请缨免除这项任务,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为朝廷立下了足够的功劳,不应该再承担这份额外的责任。
豪格的正蓝旗与罗洛浑的镶红旗则抱团取暖,也被剔除出局。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成为这个差事的牺牲品,更不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承担责任。
而福临作为正黄、镶黄两旗之主,自然更不可能亲自去运输粮草了。他的身份与地位让他无法承担这份低微的差事,更不愿意让自己的旗帜沾染上这份不吉利的任务。
一时间,议事陷入了僵局。谁也不愿意承担
看到大伙儿都不愿接这押运粮草的烫手山芋,多铎突然开口了,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显得格外清晰:“各位,我这儿有个人选。”
济尔哈朗眯起眼睛,好奇地问:“豫亲王不妨说来听听。”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,仿佛希望多铎能给出一个惊喜的答案。
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多铎,只见他一脸认真地说:“我推荐睿亲王多尔衮来当这个押粮使!”
这话一出,大殿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大伙儿都愣住了,随后反应各不相同。代善第一个跳出来反对,他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怒意:“不行,绝对不行!”
“多尔衮本就有罪在身,我们已经宽恕他让他去朝鲜筹备军需了,怎么还能再给他实职呢?”代善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不满和担忧。
“而且,我不信任多尔衮。他带兵只会坏事,粮草一旦出了问题,咱们八旗远征可就全完了。”代善的话音刚落,济尔哈朗立刻表态:“礼亲王说得对啊,我也同意。”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,仿佛已经看穿了多铎的计谋。
“我也是。”罗洛浑紧跟其后,他是代善的孙子,自然站队自家爷爷。他的声音虽然不大,但却充满了坚定。
一眨眼功夫,三旗的主事人都明确表态反对了。议政嘛,就得少数服从多数。多铎虽然手上有两旗的支持,但还差一票才能打破僵局。
此时的多铎,面容坚毅,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屈的光芒。他把目光转向了豪格,希望他能成为那关键的一票。豪格正犹豫不决呢,他的眼神在众人之间游走,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答案。